学习这篇课文时,老师和课本都将此篇定义为“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丑恶,讽刺小资产阶级”——这定义不错,但也许还有其他的意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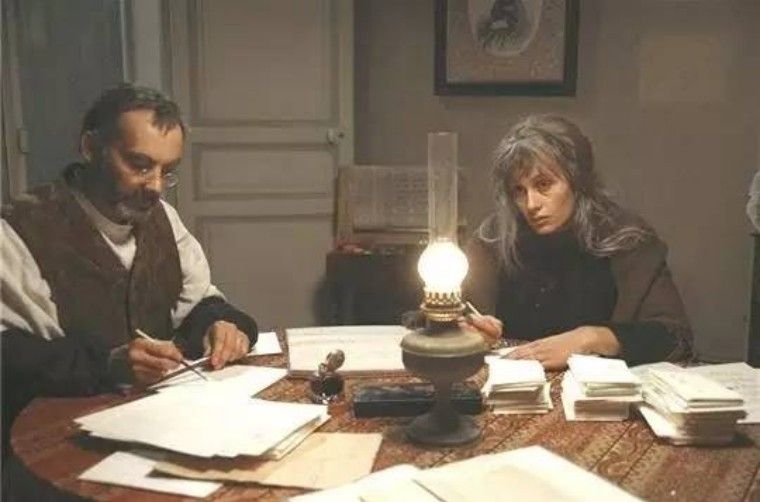
《项链》到底想表达什么?
一.通过还原【故事结局】+【导致该结局的原因】的方式描述故事,进而探寻故事内核
几乎所有故事,都可用此法来探究内核,而《项链》可以总结为:女主用10年寿命换来假珠宝,因为“某种原因”。
这里的某种原因不好总结,所有我们回头细读整篇小说,可以发现女主的行为是一连串的:
1.丈夫参加领导主办的舞会,需要身为妻子的女主作陪。
2.主角家境小资且有笔丰厚的存款,但女主没什么首饰。女主认为需要名贵首饰才能赴宴,所以在丈夫建议下,她快活的答应向朋友去借首饰。
3.女主借到项链后参与舞会,沉醉于众星捧月,弄丢项链
4.弄丢项链后,由于与朋友沟通不当,所以贷款买了同款项链归还朋友
5.无力偿还贷款,打工劳苦10年
可以看到,造成故事的原因是多段且逐步递进的。
一方面,女主面对责任没有赖账,面对负债没有去站街,面对痛苦更没有自杀,女主极勇毅。
另一方面,女主虽幻想奢华生活,但从“有笔丰厚存款,女主仍没什么首饰”“快活的答应去借首饰”可以看出女主虽有些虚荣但理性尚存:一方面她没有将家里的存款用于为虚荣买单;另一方面,当她听到可以借首饰时不但没有反感,反而是快活的答应——她此时也并非故作窘态向丈夫发难以购买首饰。
当然说她是因能借到首饰去众人面前炫耀,所以感到快活,倒也说得过去。但思想不是罪,女主的行为表明她并非彻底的虚荣拜金,又何以非弄一条项链才愿出席舞会呢?是现代人偶尔想装逼的“人之常情”吗,这个说法有些勉强,因为女主去参加的不是平民聚会,而是“上流社会”的舞会,用一条项链谈不上在这个场合装逼。
那这“某种原因”究竟是什么?女主为何一定要弄条项链才愿意去舞会?
我想原因可能是多样的:既有戴上价格昂贵的饰品才能融入该群体的压力或自卑情绪(这个压力来源于社会风气,或者说是某种教条化,同时这种风气也许是随社会发展自然形成的,也许是被厂商无中生有、暗地推动的,也许是其他方式形成的);也有想更好表现融入上流社会的趋炎附势的心态;也许还有想让自己丈夫长脸的心态……
但这些原因都不确定,故暂不提。
既然第一个办法没能探究原因,再试试第二个办法。
二.取消故事的某些设定或条件,可以更轻易的看出作者目的,以剖析故事内核
作者设定珠宝项链这个点,非常妙。
假项链的设定也是本篇小说的核心,所以我们取消这个设定试试
1.我们假设借的不是项链,而是售价差不多的车、电子设备、精美画作,那么故事的意义会变吗?
我的看法是会变。
由于丢失的东西有实在价值(画作类物品比较特别,对欣赏者它价值极高,对普通百姓它价值极低,这里不做细论),还债人生也就有了意义。故事变成了“自己犯下错误,就得自己弥补。”
与原故事相比,这个故事太俗,没有洞见生活真相。
2.那我们再假设,借来的是真·项链,故事的意义会变吗,十年还债的人生有意义吗?
可能对一些人来说,有。
这些人会实打实的认可珠宝价值,鉴定家说它值十万,那它就值十万——一种将自己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别人拍板敲定价格直接等同的概念。
对有些人来说,没有。
因为珠宝本身无实用价值,又缺乏高艺术价值,为它消耗10年寿命,很难说值得。
如果故事这样改,与1相比,多出了讽刺“小人物的虚荣心终让其饱尝恶果。”,但似乎还少了点什么。
3.既然真珠宝的还债人生已无意义,那为什么还要假珠宝结尾?同时还设定女主并非彻底虚荣之人?
这里是《项链》全篇最精妙的地方:因为假珠宝,将讽刺达到极致!
假项链不但给读者带来了一种訇然中开的震撼——女主劳苦10年变成糙妇就为了一串”垃圾“?
更将【珠宝价值几何】这个难以直接定论的问题绕开——作者直接设定女主戴的假项链,而假项链是公认的”垃圾“,可舞会上所有人(包括女主本身),都并没有为珠宝的真假而有任何态度与行为的改变。
为何一个所有人都无法辨别的饰品,就因为一句真假而价值翻天覆地,就因为一句真假让人类变换自己去其的看法?
女主为何不直接去参加舞会?
若是因为虚荣,为何不直接买一个同样美艳的假珠宝参与舞会?而是非得找富人阶级的朋友借珠宝后才愿意参加舞会?
此事不但反应出某种社会风气下形成的荒诞价值观,更抛出一个问题:女主戴一串垃圾和戴10万的珠宝项链,没改变舞会的任何事?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?
三.哪个环节出了问题
细想,只有珠宝这个环节本身有问题。
故事中,珠宝的价值更多来源于人对珠宝购买价格的惊叹,而非珠宝本身——大家其实并不能分辨真假珠宝。
这种巨大的反差,使读者在带入女主身份经历整个事件后,深陷认知平衡失调,于是为了调节这个心理平衡,开始不自主的去其他地方找平衡,进而深入反思整件事的来龙去脉,延伸出真假项链的对比思考,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以上三部分合在一起,开头提到女主的“某种原因”,答案已呼之欲出。
那么,为了一串垃圾劳苦10年固然可悲可笑,那为了什么劳苦10年就不可悲可笑?



















